
中国调解国际争端的宏愿凸显西方与其他国家间的分歧

虽然瑞士出席由中国牵头主导的全球调解机构的启动仪式为其增添了些许分量与公信,但这一由中国联同近20个立场相近国家共同发起的倡议,究竟会被视为遏制国际冲突与争端的突破性成就,还是削弱西方竞争对手影响力的手腕,外界依然存在诸多质疑。
閱讀本文繁體字版本請 點擊此處

相关内容
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中国正雄心勃勃地筹备建立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然而迄今为止各方的反应,只是凸显了西方盟友与那些将亚洲这一日益增长的经济巨头视为制衡力量的国家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中国外交部表示,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85个国家和近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约400人出席了5月30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调解院(IOMed)公约签署仪式,这也标志着该机构的正式启动。其中,仅有30多个国家现场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成为创始成员国。据报道,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是唯一签署该公约的欧洲国家。
有些国家视其为机遇。应中国邀请出席启动仪式的瑞士联邦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发表演讲时对与会代表表示,瑞士对于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下提供“务实解决方案”的倡议持赞成和支持立场。
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新成立的国际调解院强调各方自愿参与、平等协商,或有助于解决那些法律途径无法化解的争端,或能更好地代表那些在国际舞台上还缺乏话语权的国家。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中国能否说服更多国家签署该公约、加入成员国之列,并打消外界对于由中国主导的全球调解机构试图取代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建立的现有仲裁机构的疑虑,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明。
担心被解读为与中国结盟
“许多国家可能会希望避免被外界认为偏袒任何一方或在选择站队,”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致力于中国全球治理研究的研究员袁辛雨说表示:“签署一个由中国牵头主导的倡议,可能会被解读为与中国结盟。”
《南华早报》援引新华社报道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6月27日批准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并表示但凡中国涉及世界贸易组织项下的争端,将不予提交至国际调解院寻求调解。
尽管中国官方尚未正式公布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的完整名单,但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致力于减少冲突、推动有效和平建构的瑞士和平基金会(swisspeace)的联合负责人兼高级调解研究员达娜·兰道(Dana Landau)称,截至目前共有33个国家在香港签署了该公约。
瑞士在以观察员的身份调解国际争端方面已拥有逾百年的历史和经验。此次它的高调参会无疑为国际调解院的正式启动增色不少。不过,截止目前,公约签署国主要来自所谓的“全球南方”-这一概念通常指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民普遍平均收入较低,其中许多国家曾遭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

瑞士和平基金会的兰道表示,近年来,瑞士以及其他参与国际争端调解的国家正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际规则体系及其执行机构在效力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等等。她坦言:“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瑞士的调解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变得更加困难。”
近年来,瑞士的斡旋调解努力多次遭到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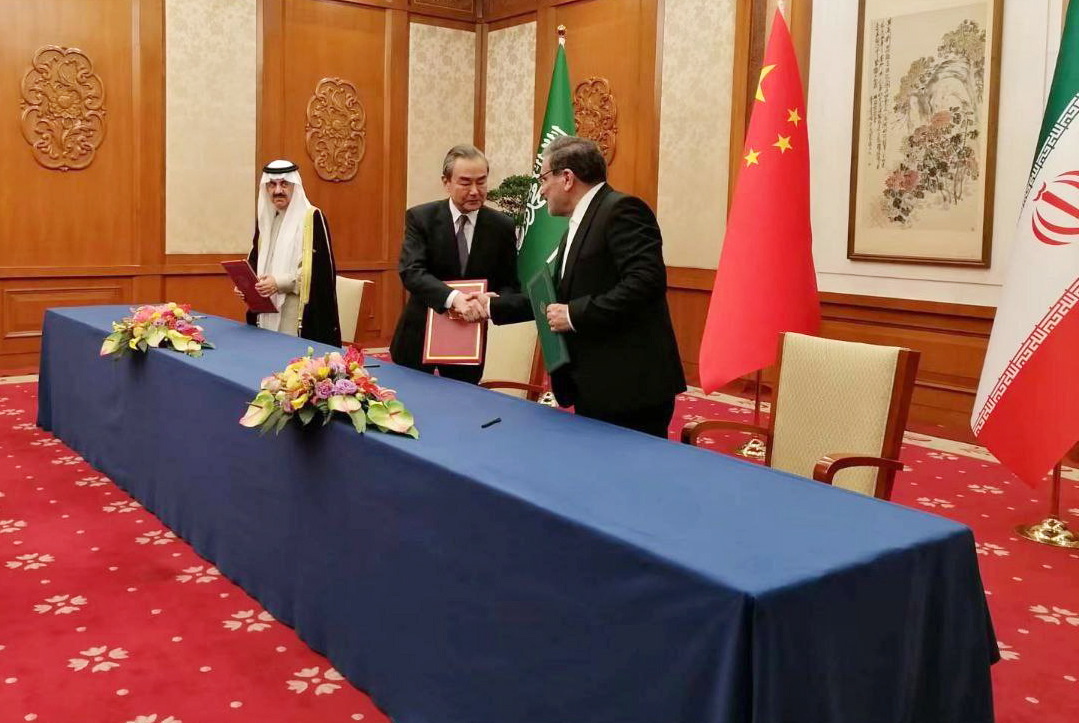
相关内容
瑞士的和平调解人形象受到挑战
为国家和个人提供调解服务
作为全球首家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将根据各方自愿原则,为不同国家间的争议、一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提供调解服务。此外,它还将处理经双方同意提交的因国际商事关系引起的纠纷。
怀疑论者可能会将这一新机构视为中国政府竭力扩大其势力范围、意图将由西方国家建立的根深蒂固的国际秩序取而代之所采取的策略。在他们看来,中国近年来类似的举措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和贷款,俄乌战争期间与俄罗斯的互动接触,以及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推动人民币作为美元的替代货币。
“国际调解院,标志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外交战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相继就中美关系撰写了多部著作的日本媒体《日经新闻》评论员秋田浩之(Hiroyuki Akita)在6月15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中国构建平行世界秩序的努力在未来持续加速,那么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全球两极分化局势。”
香港政府表示,国际调解院将设在一座殖民时期的警察局内,且该机构的地位将与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机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平起平坐”。
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针对南海仲裁案作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决定,全面否定了中国长期坚持的“九段线”内对南海海域和岛礁拥有的历史权利,并且几乎全盘认同了菲律宾方面提出的一应诉求。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参与、不承认、不接受”。中国并未参加仲裁庭,且此前曾声明,南海争议因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适用仲裁程序的限制性规定,侵犯了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因而并不适用于仲裁程序。然而,国际仲裁机构驳回了中方的这一主张。
人权记录引发担忧
“中国在侵犯人权、南海问题以及边界争端和国际裁决等方面的过往记录,显然令外界有些担忧,”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孙韵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采访时表示,“我认为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是国际调解院成立的渊源之一。(这让中方意识到)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除了诉讼和仲裁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调解。”
她在6月6日发表于该智库网站上的分析文章中写道:“无法保证其他国家会认为国际调解院会秉持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原则。”
中国官员认为,该机构是对全球现有调解磋商机构的补充。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负责国际调解院筹备工作的孙劲在一篇相关论文中表示,国际调解院是“对现有争端解决机构和方式的有益补充”。
中国对某些国家更友好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的袁辛雨分析称,相较于欧洲国家,全球南部国家更愿意加入的原因可能在于它们认为中国对其更为友好,而且它们的声音在现有国际调解和仲裁机构中未能得到充分表达。
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表示,在2022年该中心任命的仲裁员、调解员和“特设委员会成员”中,近三分之二来自西欧或北美地区。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西欧和北美地区的经济产值仅占当年全球经济产值的不到一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倘若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由中国牵头主导的国际调解机制未来恐怕很难解决其成立之初所揭示的地缘政治分歧。
“如果事实证明国际调解院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法律基础,能够有效调解国际争端和跨国商事纠纷,那么它将成为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强有力的竞争者,”孙韵在刊登于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文章中写道,“但结果如何,目前还尚无定论。”
(编辑:Tony Barrett/ac,编译自英文:张樱/xy)

相关内容
我们关于外交事务的时事通讯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